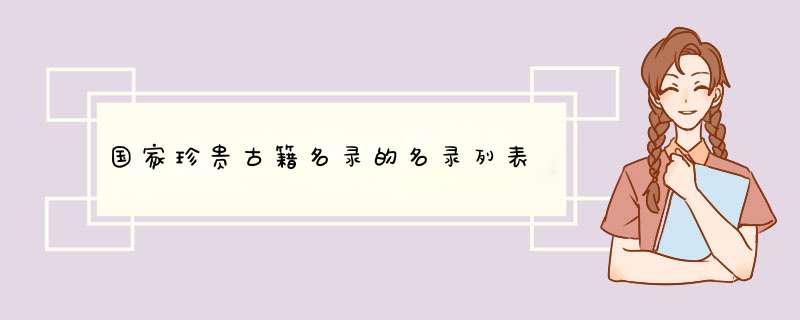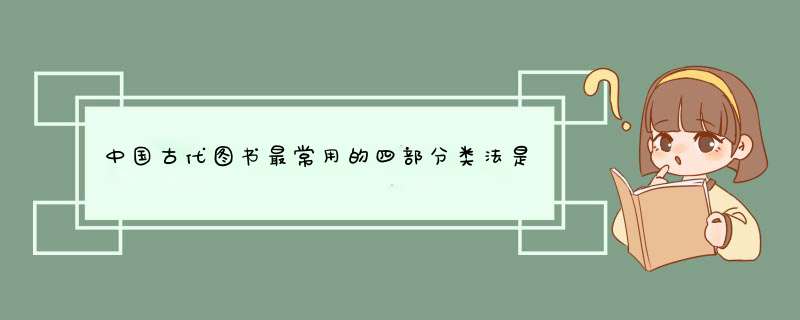古籍收藏辨别方法?

古籍善本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古籍善本收藏价值
2012年,在艺术品收藏越来越热的中国,古籍善本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话题焦点。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储存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
此后,八百二十三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保利秋拍亮相,其中最重要的《钜宋广韵》最终以3000万元落槌。
一时间,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价值潜力受到了不小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古籍收藏市场在圈内人眼中却仍是一片被低估的价值洼地。用古籍收藏家王德的话来说:“一些古本善本的价值本应是比字画都要高不少的。”
虽然医书古籍中有着无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其价格和市场认知度均还较低。其实在过去,好的古医书在价值上本是高于书画和瓷器的,如1949年前一套宋版医书的价格就远高于宋画、宋瓷。但如今,书画、瓷器的爆炒却衬托出医书古籍市场的冷清,应有的收藏及文献研究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
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升值空间巨大。专家表示,首先中医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还有极强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才能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最大程度避免现代曲解,最有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古籍由于储存难度较大,很多已经收藏古书的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医院“镇院之宝”或个人私藏珍品,越来越难收集。当然,受稀缺性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升值潜力的。
“中国通”、“汉学家”老舍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的事件,其中涉及两个美国人,他们是叔侄关系。在中国,我的侄子是北京一个福音教会的牧师,他以传道为生。我叔叔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他相当牛逼。可能是,也可能是国会议员之类的重要人物,从他一开口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道语气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偷了别人的牛,耳朵被割掉了,所以逃到中国,卖鸦片什么的,赚了很多钱。回到家乡后,以前叫他流氓的亲戚朋友都叫他中国通”。从此“在他面前,人们一致避免说‘耳朵’二字,都受到了启发。去中国发财,不管有一只耳朵还是两只耳朵。生活太艰难了,圣诞节都吃不到烤火鸡。舅舅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该去中国了!在这里,圣诞节连烤火鸡都吃不到;在那里,你每天都可以吃到肥母鸡和大鸡蛋!你永远也雇不起这里的仆人;在那里,你至少可以用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仆人!走吧!“所以,牛牧师,其实挺窝囊的,到了北京就趾高气扬了。不仅“有自己的小房子,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而且鸡肉和鸡蛋这么便宜”,以及“他几乎每三天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和叔叔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中国通”一词逐渐被改名为“汉学家”,是因为它总是勾起百余年来外国列强侵略的黑暗记忆,不那么好听。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中国专家”还是“汉学家”,都是流氓,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来中国打秋风的“汉学家”,脸上真的是谄媚之色。尤其是我这一行的一些人,在这些外国人身边谄媚、微笑、肩扛的仆人,更是不堪入目。就跟老舍那个崇洋媚外的老板一样,腋下夹着一本《圣经》,整天跟着牛神父扮傻子,讲讨好他。他就是想捞几个奖励,让他在便宜的店里买点红烧肉杂碎,拿着干荷叶回家白喝两杯。他们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许多大哥的兄弟,一个严肃的人劝他,“大哥!给老祖宗留点面子,哪怕一点点!别拿外国人吓唬人了,那是不要脸!不要脸!”慈禧从污水缸里捞出乞丐。大概是大哥跟着牛神父吃喝的时候,一个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了北京。这个人不是老舍笔下牛牧师那样的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一个真正的英国贵族,有着男爵的头衔。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约克郡,人们首先称他为先生,然后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卒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专家”,是一个流氓头脑的“汉学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时代的北京人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些曾经浑水摸鱼的“中国通”和“汉学家”,早就被扫进了垃圾堆。不过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书先在香港出版,然后在台湾省出版。然后在我们那里,一些贪利忘义的文化人也把这个英国老流浪汉从泔水缸里搅了出来。可想而知,这本与慈禧太后“同床共枕”的书之所以大受欢迎,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不少钱,连做梦都笑出声来。
但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角度来看,指名道姓糟蹋死人,给外国人犯错,给祖先挖坟,都是洪水猛兽。但是,没有办法!在海洋里的时候没有心肝,慈禧一躺下就要挨枪子。但是,细想起来,西方世界对付中国的手段、招数、招数、招数,连一只螃蟹都不如,真是可笑。从18世纪的炮舰政策,到19世纪的殖民蚕食,20世纪的封锁绞杀,21世纪的分化肢解,现在已经堕落到用这种自慰的文学作品来抹黑中国,在西方宣扬优越的沙文主义,标榜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大概,做这个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如果鸦片战争中的英军指挥官,比如陆毅、巴斯贾里,或者八国联军总司令维德西,从地下活着出来,看到他们的后代,又会愤怒。虚构新闻的祖师爷巴克斯要来中国碰运气的原因,和老舍笔下的牛神父的叔叔在中国贩毒差不多。神父的叔叔因为偷牛在美国混不下去,巴克斯因为债务在英国混不下去。他们同路。然而,牛牧师的叔叔因偷牛被割掉了耳朵,巴克斯负债高达32000英镑。他一抹脸宣布破产,就逃到了中国。按照18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每英镑含纯金732238克,差不多可以买3万头牛。但是,他的头发是完整的,他的耳朵在他的头上是完整的。他出现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这里曾经是秦春宫。原来巴克斯来到中国,走的是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路子,希望能在这么肥的政府里谋得一份差事。不知道是因为他宣告破产的不良记录,还是因为他的放荡丑闻。考虑到他精通中文,赫德顺势将他推荐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就在这个时候,1898年9月,戊戌变法那一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住在颐和园的老佛爷一举扼杀了光绪新政,下令逮捕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菜市口处决了谭嗣同等六位先生。当时,《泰晤士报》的远东特派记者莫正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旅行。于是,越权的巴克斯以莫的名义,发表了0755到79000的一系列京电,其中不乏“第一手”消息,捏造独家新闻,惑宫。70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考证,郑重声明“0755年至79000年关于北京康梁变法及随后政变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是巴克斯为了谋生而编造的”。文学允许虚构,但文学不能虚构。新闻一定是真的,但不是真的就能算新闻吗?那是谣言。一百多年来,西方媒体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人心,挑拨离间看来这是一脉相承的,有渊源的。族长是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HughTerefeRoper的结论,即“捏造”一词是伪造者生活的关键。既一针见血,又揭露了西方媒体的虚伪。如果说巴隆老师的捏造是为了“谋生”,至少要做出让人相信的样子,而他同学的后续一代,那些西方媒体的捏造,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等不及了。比酒神巴克斯还厉害。”祝你平安!但愿世界不太平!“辛亥革命后,中国《泰晤士报》记者莫李勋被中华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他没有继续与这位虚构的作家合作,而是由另一位接替他的中国《泰晤士报》记者蒲兰从上海调到北京。
不管是联系还是一丘之貉,这两个人吃中国,嚼中国,恨中国,诅咒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一见如故,气味相投,并在某一点上相遇。很快,一本名为《泰晤士报》,又名《泰晤士报》的书于1910年出版。另一本《慈禧外传》,又名《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于1914年。清朝刚亡,尸骨未寒,巴克斯的杜撰作品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出现,这个侥幸,是最敏锐,最深刻,最及时的。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的身份能稳操胜券地落入他的口袋吗?特别是《清室外记》,以《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的“独家资料”记录了庚子事变的全过程。这本书不仅展示了清廷高层的内部斗争,也暴露了皇帝和皇后之间的矛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被披露,几乎是一部太后滥交的性生活史。这本书的出版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出版后的第一年,就重印了十多次。然而,在民国初年,出版商们坚持自己的规则。虽然是赚钱的好生意,但是翻译的并不快,赚的也不少。就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本书一无所知的时候,有个叫辜鸿铭的,第一个熟知西方,比较精通汉学的名人,对这本书表示“极大愤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辜鸿铭对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他们《慈禧外传》的憎恨,源于他对西方人与生俱来的对皇族和君主荣誉的珍惜和尊重的钦佩。“其实,这个天真的老夫子并不知道,这些穿着晚礼服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如果不是野蛮人,至少比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彼此都不如。顾老师,殖民者把你当成劣等民族。你还想得到他最起码的尊重吗?在西方,的确有很多高尚的人,但也有更多忘恩负义的混蛋。在老舍老师的《景善日记》中,一只耳朵的美国人这样开导在北京传教的失败者侄子:“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你制造的麻烦越多,对我们越有利!如果有大的骚动,我们会派出军队。你害怕什么?问问你的上帝,是这样吗?告诉你最有用的:如果没有麻烦,你就做一两个吧!你想避开那里吗?你发泄了牧师的愤怒!祝你平安!但愿世界不太平!“以此类推,我们知道普兰和巴克斯毁了慈禧,埋了中国,不过是激进派的老把戏。所以这本风靡欧美的书,把慈禧的形象设定为丑陋、不道德,一直定格至今。后人对西太平洋的负面印象,不好的印象,都是0755年到79000年这两个“中国通”影响的。好在慈禧太后的前女官余德龄用英文出版了《慈禧外传》,让辜鸿铭如释重负,大加赞赏,还为其写了英文书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正红旗下》上。他说,“这本朴实无华的书,在向世人展示满族人的真实情况方面,远胜于其他任何一本名著。”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两位善于发明的“汉学家”的。但如果这位国内外著名的大师看到了巴克斯写的第三本书,《慈禧外传》,我想这位老教师不可能如此淡定。至于那些“扭曲理智”的西方媒体,从那以后,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编造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符合美国大叔对侄子的“启蒙”和巴克斯男爵的“捏造”精神。检查《清宫禁二年纪》《国际评论》没有原始的《太后与我》。第17章引用的《景善日记》,被视为舶来品的独家秘籍,其实是巴克斯闭门造车的“杜撰”。他的合作伙伴、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普兰德说,他本人没有见过这本日记的中文手稿。
普兰德后来将英文手稿赠送给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照例要求提供中文译本原件。但是,不知道当时是越洋电话难打,还是巴克斯心里有鬼。普兰德得到的回答是原作已经卖出去了,然后说是不小心掉进炉子里烧掉了。骗子经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欲盖弥彰,雪上加霜。中国社科院学者丁明南断言:“《慈禧外传》是假的,巴克斯特发现日记的全过程也是假的。这只是巴克豪斯故意玩的骗人的把戏。”第一,作为日记的一种风格,除了像博客或者微博,而且是给人看的,大部分日记都是相当私密的。但是,在这本日记中,我们看不到一点关于主人公的私生活、内心活动、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内容,更谈不上那些外人看不够的隐秘内容。第二,主人公景山当时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官员。他辩称,他可能会接触到一些高级官员,但他成了执政当局的人物路路通。从这本相当于现场新闻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高官贵族,不论派系,都和他走得很近,自始至终无话不谈。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就更不可思议了。第三,一个不坐冷板凳的右侍郎,或者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决不是军部的炙手可热的张静可比的。他不能在新闻的源头,更不能卷入政治纷争。尤其是他无法监听各方动态,了解内外消息,知道老佛爷的情绪,了解人们的反应。一个旗官,上不去下不去,坚守岗位,还怕。他怎么敢卷入政治漩涡,闹事?我一直以为这样一个“好奇”的性格就是当时巴克斯的角色。第四,最不合理的是,进士出身的官员,至少要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诗词歌赋,四时、八时、感伤、娱乐、附庸风雅。这也是中国文人最喜欢的表演。就算是一个狗屁官员,如果他写不出两句诗,写不出两个字,喝不了两壶酒,搞不出风流韵事,还能在官场混下去吗?百密一疏,巴克斯没有弥补这些漏洞。任何细节上的疏忽,最终都会导致全盘皆输。想拿到教授头衔。如果说,巴克斯以莫里斯的名义,于《景善日记》在北京发表了关于戊戌变法的文本,开始了他虚构写作的第一步;然后庚子事件中,基本上是文物大盗的巴克斯抢了好几屋的货,这应该是他在中国挖到的第一桶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允许士兵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镇压人民。北京成了人间地狱。而在这群成群结队四处侦察的盗匪中,巴克斯也率领着一只老虎队浑水摸鱼。他带领的抢劫小分队在大街小巷游荡,主要袭击皇家官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威胁,用他流利的中文招摇撞骗。据他在回忆录中供述,短短几天内,他就虚张声势,哄抢盗走青铜器600余件,善本2万余册,名家书画数百件。这是一个专业的小偷。他知道什么该偷,什么不该偷。他甚至用偷来的珠宝和玉器与盟军士兵交换文物。这个当年才27岁的男孩,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有一天能把自己的赃物献给自己的大不列颠王国,实现光荣回国的梦想。1913年8月,已经打下坚实基础的巴克斯,资本雄厚,名声响亮,信心满满,开始向伦敦发起挑战。通过海运,他将重约8吨的藏品,包括27000份中国古代手稿,以及书画卷轴、古籍和青铜器等文物运往伦敦。
当然这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更耸人听闻的是,巴克斯宣布将自己的全部藏品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以回报他的栽培。中国收藏的东西100%都是赃物,充满了小偷的味道,但接受者牛津大学并没有嫌弃,欣然接受。但牛津大学也有其“牛筋”或“牛劲”,即不同意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并授予其教授头衔。东西,我要;教授,没有。首先,他没有在牛津完成学业;其次,他没有国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做一个普通的汉学家,可以。你想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不会吧!巴克斯是退而求其次,看他能不能拿到荣誉文学硕士学位?那些负责学校行政的老人研究了又研究,最后也没有结果。一气之下,他买了一张去天津大沽的车票,回到北京,隐居在西城什楚马街的一个四合院里,死在了中国。《疯狂的涂鸦》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巴克斯在奥地利驻华使馆避难,结识了瑞士人贺普利。何普利建议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于是有了这个《景善日记》。在这本书中,被视为疯子和骗子的巴克斯声称与许多名人发生过同性恋关系,包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尔兹利、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异性交往的是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除了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还发明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诞不经,驴唇不对马嘴。他们甚至比现在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走火入魔。如大学生孙家鼐与邮传部大臣合谋,与作者“捉奸太后于床”,但未得逞;春福晋亲王指使厨房里的厨师用砒霜毒死作者的“奸夫”,但未果;载沣、奕_、军务大臣余浪、内务府办公厅大臣许氏等策划废太后,迎光绪“回府”;慈禧得知阴谋,指派太监勒死光绪,意图立普伦为帝,处死袁世凯;后来召见时,袁世凯拔出手枪,“向太后开了三枪”你不能不佩服这个老小子。他能想起来真的很可惜。评论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说,“巴克斯与王太后的这些荒唐的性游戏的肆意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相遇的荒唐细节,使他极度兴奋的完全精神错乱的性幻想变得无聊。几十年前开始的机智顽皮的讽刺,现在已经退化成疯狂的涂鸦。”最早指出酒神巴克斯是“被发明”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他的著作《泰晤士报》中建议将这本书的书名改为《太后与我》更为恰当。就连信奉巴克斯的霍普利也不得不在编辑完这篇手稿后写的后记中坦承:“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被记忆混乱所扭曲,在多大程度上被添加了想象,这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的《酒神巴克斯》《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在沉迷于性幻想的男爵还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即使巴克斯在1944年去世后,也没有为他出版这本书的意思。他只是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手稿打出来,复印了许多份,存放在英美几所大学的图书馆里。1973年,赫普利也去世了。这本书《太后与我》一直被搁置在图书馆里。这本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的书,在2011年似乎声音有点大。首先是英文版,然后是繁体中文版,再然后是简体中文版,一个接一个。很热闹。的出现可能只是一部分人想发财想疯了的偶然事件,也可能不是反华政客刻意安排的。而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和精神攻势,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
试想,老舍老师的《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当年大哥曾经说过的“连我们皇帝都怕洋人”,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带着种族偏见、殖民心态、白人至上、恃强凌弱习惯的西方人,是不甘心的,是沮丧的,是不安的。更何况,面对自身的不可阻挡的衰落,面对中国的不可阻挡的崛起,那种发自心底的失落感、挫败感、酸酸的味道,堵塞了我的肺、肺、五脏六腑,当然是难受的、不愉快的、不快乐的。所以,就像唐朝柳宗元寓言里的那头驴,先运到贵州的大坝上,绝对有可能舔你两下,把你恶心,把你弄乱,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把你弄穷。
本文2023-08-04 01:32:4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5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