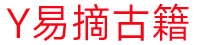今天所读《论语》是汉代删改本?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本其名义到底所指为何,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有:
(1)班固:《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2)刘向:《别录》: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3)刘熙:《释名·释典艺》:
“《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4)何异孙:《十一经问对》:
“《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以上诸说中,今人多持《汉书·艺文志》的观点。但笔者认为,除第(4)种观点不能赞同之外,其余看法其实是可以兼容的。
《艺文志》关于《论语》之名义的解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界定了《论语》所记之“语”的范围。其中既有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又包括了时人、弟子之间的言语,但这些言语又必须为孔子所“接闻”即间接为孔子所知。不过,以此而言,《论语》中有些言论发生于孔子没后,但大多与对孔子的评价相关,故“接闻”之语似可作更加宽泛的理解,即为孔子间接所知、或与孔子相关之语。二是指出了《论语》作为一个文本所产生的过程。由于孔子的学生众多,且他们与孔子的交流并不是在同一时空场所进行的,因而发生“弟子各有所记”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有七十二伴随登堂入室的弟子,便会有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这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确认和证明“各有所记”之文本的真实性?如果不能确认这一点,则《论语》作为一种文本的权威性就无法得以保障,从而也就无法产生“圣人之言”的“可畏”性影响。所以,孔子没后,其门人之间的相互“辑而论纂”不仅是事实,而且这一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这一点可以从“孔子死后,儒为分八”的历史事实中得到佐证,而儒学这种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孔子门人之间在文本上的各有所本是密切相关的。到西汉时,就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三种本子流行。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今所本之《论语》应该视为战国至东汉期间儒家后学所达成的一种有关夫子言行记载的文本共识。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欲达成《论语》这样的文本共识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今所本之《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将《古论语》与《张侯论》合二为一的产物,而《张侯论》则恰恰是西汉末年的安昌侯张禹合《鲁论》与《齐论》的结果。
《汉书·艺文志》关于《论语》的上述说明为我们理解《论语》之名义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线索。首先,从《论语》作为文本共识的产生过程来看,《论语》之“论”是指“辑而论纂”而言,这种“辑而论纂”也相当于佛教文献史上的佛经集结。换言之,“论”之为词具有反映《论语》作为文本的产生方式的意义在内,有讨论、论断(如政治家张禹的《张侯论》,学者郑玄的《论语》)的意思。“论语”之义,也就是指一种经过讨论而为不断扩大的孔子后学所认可的有关孔子言语的文本。
其次,正因为《论语》是经过讨论而达成的一种文本共识,那么也就意味着“论语”之“语”作为一种言语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学术认同的基础,从而也就具有一种与一般的日常话语不同的意蕴。所谓学术认同,在这里是指对于《论语》之为孔子的言语集的真实性表示赞同与认可。孔子的弟子虽“各有所记”,“所记”之中必有出入与差异,甚至出现你有我无、我有你无的情况,但是经过讨论,大家对于《论语》文本中的内容持有一种基本的确信,即“这些话确是孔子说过的”,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作为《论语》文本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怀疑孔子所言的真理性。
第三,对一种文本的认同除了学术认同以外,还内在包含了文化认同的因素。所谓文化认同在这里是指根据什么标准去确认某一话语为孔子所说,而其它则不是孔子所言。因为,尽管《论语》作为一种“语”由于是经过“论”而产生的,它之为孔子之言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就孔子一生说过的话而论,肯定不止我们所看到的《论语》那样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有《论语》中的内容才是可以证实的孔子言论呢?肯定不是。有些话虽为孔子所言,且可以得到证实,但不一定载入了文本之中。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儒家后学编纂《论语》文本的过程中,除了对于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证之外,还把自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融入其中,甚至还抱有一种建构“圣言之言”文本的理想。这就是说,凡是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孔子思想的言论,不管它是否为孔子所言,概不收入;或者凡有损于“圣人之言”形象的,尽管确为孔子所言,也不予以收录。这种文化思想的认同标准应该是《论语》文本在数量上很少的根本原因所在。我认为,正是《论语》文本形式上的这一特征表明:“论语”之“论”不仅意味着一种文本内容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论语》作为一种“话语”的权威性,易言之,《论语》所记之夫子之言具有真理之言、“圣人之言”的肯定性价值,因而刘向在《别录》中所谓“《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第四,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古汉语,“论”与“语”作为两个独立的词,虽有联系,但也有区别。“论”,《说文》:“论,议也。从言仑。”仑,条理、伦次之意。故“论”之为“言”确具有条理之言的意义,而“语”则不一定有条理之言,不一定经得分析和推敲。而“语”之为“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逻辑性,二是具有事实性。就前者而言,《论语》文本中的“语”多指“问答”之语而言,而“问答”之语在语言形式上具有口语化特征,且由于“问答”作为一种对话形式总与具体的场景和议题相联系,故而言语的“所指”功能十分突出,譬如孔子谈仁,对颜回、子贡、樊须、子路等弟子便有不同的回答,甚至同一个弟子如樊须,因 “问仁” 的时空境遇不同,孔子的回答也不同。换言之,“问答”者主体的个性特征、问答时所处的场景等因素,皆是《论语》的文本构成条件之一。这一点虽赋予了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但同时也不利于思想的系统性达成。孔子之所以反复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恐怕就是有见于此。既然孔子所“语”皆是围绕着“一”这个中心而展开,故其“语”——尽管是一种“问答”之语——心定是符合语言逻辑性要求的话语,是一种“思”之“语”,而非无伦次之语。
语言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对于思想系统性的构建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但哲理的强制性则主要源自于它的实践性。孔子以“述而不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自觉地拒绝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做固然与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尊重有关,但也与他对于“文胜于质”的思想学术风气的不满有联系。孔子十分重视言行之间的统一,所以他的“立言”总是与实践的可操作性紧密相连,所谓“因材施教”,其本质就在于使“知之”而后能“行之”。程子说:“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四书集注·论语》)“自然”,就是指孔子的话贴近于每个读者的经验,他所回答的问答正是自己生活中的疑问,令闻者释然。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孔子所“语”,是就人、就事之“语”,简言之,就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之“语”。也只有这种“语”,才真正称得上“论”。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评价司马相如词赋时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语可论者”之说表明:在太史公看来,相如之“语”既有“可论者”,也有“不可论者”。“不可论者”,即“虚辞滥说”也,也就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辞。而“可论者”,无疑是指与实际相联系的话语。在《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书”如其“人”,意味着“书”是人的另一种人格化存在形式,是言与行高度一致化的结果。所以,《论语》之“语”是一种“可论”之“语”,是一种既符合思想的逻辑性,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语”。从语法的角度说,“论语”是一种“论之语”,“论”作为定词,具有对主词“语”的肯定意蕴在内。
从“语可论者”的角度来分析《论语》之名义,可以看出:一方面,《论语》之“语”作为孔子所说过的话语这一客观存在事实本身就具有“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孔子所有之“语”中也只有经过了孔子后学的“议论”后,认为那些具有“论”的性质的言语才谓之为“论语”。这就是说,《论语》之“论”既是孔子之“语”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质,又是孔子后学其中特别是《论语》文本编纂者的一种“论”。因为,如前所述,孔子一生所言决非《论语》之数,而之所以只有这么多,是因为孔子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可论”之语。对此,孔子本人也有自觉,如《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又如《述而》载:因为说了鲁昭公“知礼”的错误言论而为陈司败所指出,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承认自己所说的话中有“戏言”,有时甚至还说了错误之言,这些可能只是《论语》中提及的孔子之言中“不可论者”的少数例子。之所以为编纂者所保留,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它们无损于孔子作为“圣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编纂者想借此透露出编辑孔子言论的标准,即“语可论者”方能选入文本之中。
综上所述,从“语可论者”的角度来界定《论语》之名义,可以兼容《艺文志》、《别录》及《释名》等文献关于该问题的阐释。因为,“可论”之“语”是经过孔子后学的“议论”编纂认可之“语”(《艺文志》),是经得起逻辑推敲和实践检验之“语”,故而非无伦次之“语”(《释名》),当然是有益于社会之“语”即“善言”(《别录》)。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4]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
[5]张岱年:《孔子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6]陈科华:《孔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估计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都会去研究研究的吧。这个的话,就不是N人了,是NN人。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7) 钱峻《论语浅讲》。
《论语译注》(杨伯峻)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iyye
书名:论语译注
作者:杨伯峻
豆瓣评分:92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9-10-1
页数:308
内容简介:
《论语译注》内容包括:试论孔子、导言、例言、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等。
作者简介:
杨伯峻(1909~1992),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著名语言学家。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
《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作者是孔丘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7ptk
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今文《论语》、古文《论语》和《论语》注释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形成两个学派,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秦代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几濒毁灭,幸存的儒生坚守儒家衣冠和礼仪,依靠口耳相传,传述他们的经书。汉初开书禁,搜求和写录古籍,立官学传授;整理出写本。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当时的简笔字)书写,称今文经。后来,又出现了一部分用战国时代通行的篆文书写的经籍,称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只是书写的字体不同,篇章文句和文字训释也有差异。汉代传经重视师法门户,于是形成对立的学派。
汉代流传的《论语》,也有今文和古文之分。
今文《论语》有两家,鲁人所传者称《鲁论》,齐人所传者称《齐论》。
《鲁论》凡20篇,《齐论》凡22篇。《齐论》多出的两篇,《汉书艺文志》自注曰:“多《问王》、《知道》”;学者们又怀疑“问王”为“问玉”之误。不过这两篇今皆不存,是非已很难稽考。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齐论》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现在我们只能知道《齐论》的训释之词较《鲁论》多。
古文《论语》只有一家,据说是和古文《尚书》一同为鲁恭王在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这事和古文《尚书》一样真伪难辨,我们可以不再管前人的这些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汉书艺文志》记“《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古文《论语》简称《古论》,篇名比《鲁论》多一篇,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古论》的文字与《鲁论》、《齐论》也有四百多字不同。《鲁论》、《齐论》最初各有师传,相信《古论》的人较少。
我们现在流传的版本,不是《鲁论》,不是《齐论》,也不是《古论》,而是《张侯论》。
张侯,指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他先传《鲁论》,又讲习《齐论》,把这两个版本融合为一,篇目以《鲁论》为根据,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他的这个本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便通行天下。东汉灵帝时代刻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魏何晏又以郑玄注为本,作《论语集解》,这就是通行的宋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版本。
《论语》内容丰富而文字简约,这为注释和讲解留下发挥的天地,古代解释《论语》的书达三千余种,下面择其最主要的略作叙录。
《汉书艺文志》记汉人传授《论语》12家、229篇;《隋书经籍志》补记汉时周威、包咸为《张侯论》作章句,马融作训诂。但这些注释已经全部亡佚。东汉末年郑玄作的《论语注》,现残存一部分,尚可看到《齐论》、《鲁论》、《古论》的一些面貌。
《隋书经籍志》记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均曾撰《论语》义说,这些也已经亡佚。《论语集解》撰者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五人,“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这个注释本集孔安国、包咸、周威、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汉魏各家古注,是现存最古的注本。梁皇侃为《集解》又作《论语义疏》,再集魏晋数十家之说为何晏《集解》申说,唐代传入日本,为日人所推重。
宋邢昺为何晏《集解》作新疏(《四库全书》作《论语正义》),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详于章句训诂和名器事物,“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郑堂读书记》)。宋人编《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即题为“何晏集解”、“邢昺正义”,合称《论语注疏》,通行至今。
南宋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四书”,为之集注。其中,《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也较为通俗易解。朱注是明清两代科举用书,为读书人所本,影响很大,但理学气味较浓。清人毛奇龄《论语集求篇》专为驳斥朱熹《章句》之作。该书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反复推勘,以证朱注之谬;但其中也有些地方强生枝节,半是半非,甚至有立论不足为据者。参读时须加辨别。
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他认为:皇疏“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疏“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后序》)他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力求实事求是,折中大体得当。刘氏于道光八年(1828)开始著述此书,1855年于书将垂成时病故,由其子刘恭冕继续写,于同治四年(1865)全书写定,前后历时三十八年。这部书集前人注疏之大成,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近人杨树达撰《论语疏证》,汇集三国以前古籍中与《论语》有关资料,排比于《论语》原文章句之下,间下己意以为按语。主旨是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引书约70种。陈寅恪《序》称:“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近人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大成的名作,引录典籍680种,取舍谨严,博而不滥,凡120万言,体例周备,疏解详明,便于披阅。
近人钱穆诠释《论语》的专著《论语新解》,以篇次为序,对原文注释、解析、串讲并白话试译,不乏新见,在港台及海外较流行。
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包括原文、注释、译文、余论四部分,并附《论语辞典》,是当代较好的白话译本,流传广泛,但仍有一些阙误。
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