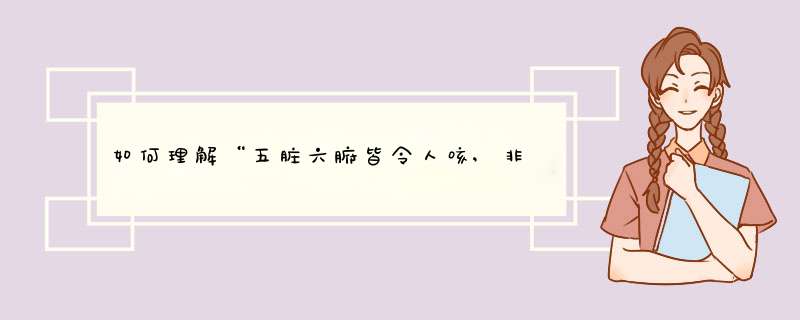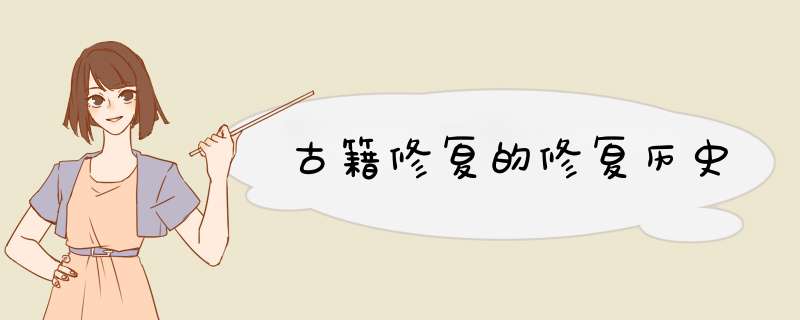小议文物 这个题目的文章怎么写

文物与文献小议
根据出土文物来订正人们对古书的误解,其例甚早。如《南史·刘杳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杳)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羹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栖樽作栖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代,郑玄的学说被视为“三礼”之学的权威,可是在出土的古器物面前,人们也不得不改正他的说法。出土的古器物是如此,出土的帛书、竹简更是如此。例如《战国策·赵策》中的“左史触耆”,清代学者王念孙已指出当从《史记》作“触龙言”,而此说的被确证,却由于帛书的出土。
我们阅读古书,有时遇到难解之处,其原因各各不同,有些可能是字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找到版本根据或其他旁证加以校改,这当然是很理想的。有时找不到确切的根据,前人往往使用“理校”的办法,即通过推理解决疑问。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有时也难免出错。例如《老子》河上公注本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二句,“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又说:“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清人俞樾根据唐景龙碑文作“以道作人主者”,认为是古本,又据“河上公”注中“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的话,认为“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则是人臣以道辅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辅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似,又涉注文辅佐字而误耳”(《诸子平议》卷八)。这见解看来很有理,其实未可信从。因为这里的“佐”字,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本《老子》作“差”,亦即“佐”之假借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则径作“佐”字。既然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均作“佐”,那么据景龙碑文及“河上公”注,恐不妥。所以阅读古籍如果仅仅用力于书面材料还是不够的,必须关心考古发掘的新资料。
然而,要理解发现的新出土资料,还是要熟习已有的文献资料。例如:最近一期《文史知识》上刊登了郑慧生先生的《张楚正义》一文,他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有“张楚”二字,联系《史证》中《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中提到“张楚”的话加以考察,并且还注意到了同书《天官书》中“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的话,指出“‘张楚’为‘张大楚国’,是一场复立楚国的运动。它既非国名,又非王号”,当从《集解》和《索隐》所引李奇说。这结论是很令人信服的。我们读《史记》,对《天官书》往往不甚用心,因为这是专门之学,治文史的人往往不大懂,读起来也就不如本纪、世家与列传认真,可是最能说明“张楚”二字含义的话,正在这篇中。这说明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出土文物,还有赖于我们对文献资料的熟习。所以王国维当年提出要“双重论证”的办法,确实是十分正确的。
前面说的还只是就一般阅读古书而言,如果具体到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要理解出土文物,恐怕更需要对文献下功夫。即敦煌出土的唐永隆写本《文选·西京赋》而论,其中就有许多古字,如拂拂的“拂”字,这里作“铃”,乃从篆文“臀”字形变而来,如果我们不读《说文》,也难于辨认。更重要的是近年出土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联系许多典籍也很难深刻理解,例如近年出土的《神乌傅(赋)》,其实是一篇很好的汉代俗赋,如果不联系曹植的《鹤雀赋》、敦煌俗赋《燕子赋》以及《诗经·鹤钨》、汉乐府《乌生》、《飞来双白鹊》等禽言诗,也很难阐明其意义。所以我们阅读古籍、研究文学史,都必须注意考古的新发现,也更需要对古籍多下功夫。
家风传承新颖有诗意的题目有如下:
1、何必乱作揖
2、人生贵在行胸臆
3、大智闲闲
4、心之至道,一苇以航
5、暾将出兮东方
6、何处青山不染尘
7、自飞晴野雪朦朦
7、自飞晴野雪朦朦
8、待踏马蹄清夜月
9、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10、霁云不改心中月
11、远近结合,感受自然
12、舍一朝风月,得万古长空
13、仰观宇宙,俯察万物
14、以我之力,追我所愿
15、人生无极限,奇迹会出现
16、潜心于学术,造福于未来
17、门后花开,一路前行
18、和苏轼一起赏月
19、微笑是一把神奇的钥匙
20、试问千年有多重、
小议文物 这个题目的文章怎么写
本文2023-10-03 02:25:4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91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