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偶、对仗及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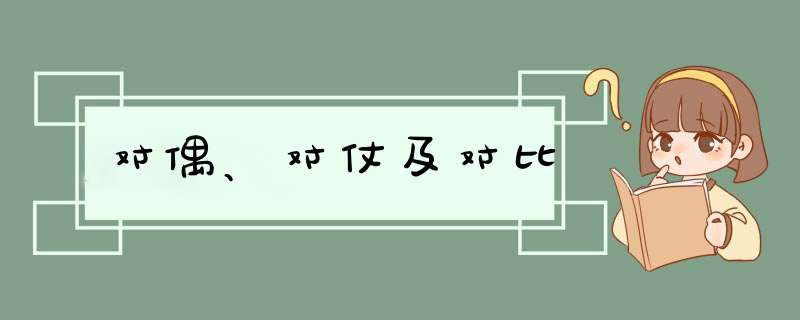
这是三种修辞方式。之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说,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对”字在其中,且有一定关系;同时,也由于有部分人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影响了自如地运用表达,所以有说说的必要。
先说对偶和对仗。
对偶和对仗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方法,虽然都是两两相对的,却有较大的区别。
从应用的范围来说,对仗不如对偶应用得那么广。对偶无论在什么文体中都可以用,字数、句式等都不受限制,非常灵活,而对仗却存在诸多限制。
对偶 是将两个词组或句子成对地排列起来的一种修辞方法,一般由出句和对句组成;这两句必须字数相等,结构相同,且意义紧密相连,或相关,或相对,或相反。
在文章中用对偶,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恐怕要数《滕王阁序》了。
如:“披绣闼,俯雕甍。” (推开雕花的阁门,俯视彩饰的屋脊。)这是三个字的。出句“披绣闼”是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动宾结构,对句“俯雕甍”也是一样。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运不畅顺,命途多艰险。冯唐容易老,李广难封侯。)这是四个字的主谓结构。
又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渔船在晚归时唱歌,歌声响遍鄱阳湖畔;雁行被寒气所惊扰,叫声直达衡南水边。)上下句都是四六的句式,十个字;结构上完全一致。
再如:“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物里精华是上天的珍宝,宝剑的光芒一直冲上牛斗二星的区间;人中俊杰是大地的灵气,好客的陈蕃专为高雅的徐孺设下几榻。)这是四七言对偶。
还有《史记》中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鸿门宴》)、《醉翁亭记》中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等,都是意义相关的对偶。
现代文中运用对偶的也不鲜见。如台湾作家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就有多句对偶:“山也虚无,树也缥缈”“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等。
即使是民间俗语,对偶句也占了大部分:
菜刀越磨越快,脑子越用越灵。
柿子拣软的捏,骨头挑硬的啃。
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快马也要响鞭催,响鼓也须重锤敲。
……
对偶的种类 有正对、反对和串对(流水对)。
正对为上下句意思相似、相近、相补、相称的对偶句,如上述所举的例子,都属正对。
反对是上下句意思相对、相反的对偶句,如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又如杭州岳王庙殿的对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串对也称流水对,是上下句的意思具有承接、因果、递进、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对偶句,如:“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因果关系)“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承接关系)等。
根据上下句的形式又可以把对偶分为严对和宽对。
严对是指字数相等、词性相同、结构相同(含词性及构成成分、构成方式)、平仄相对、不重复用字的对偶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宽对是指相对要求宽松的对偶句,即相对于严对的五条要求只要达到一部分就可以。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等。
对偶的结构也有几种:
成分对偶。即在句中某些成分是对偶的。如:“然而我的坏处,是在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 ,而后者尤与适宜不合。”加粗的部分就是句中的成分对偶。
句子对偶。上面举例很多,不再赘述。
还有本句自对的对偶。如“水落石出”、“词工句丽”、“虎啸猿啼”等等。
说完对偶再说对仗。
对仗 的适用范围非常小,是诗词中的对偶句,且属于严对。
跟对偶相比,对仗有诸多限制。
首先,它必须在诗词中一定的位置出现。如律诗中的颈联、颔联;在词中也有规定的位置,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次,在不同格律的诗词中,字数有一定之规。如“七律”中的对仗,每句只能七个字,如“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忆江南》词中,三四句的对仗同样要求七个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再次,对仗对结构的要求更严格,不仅句子结构要相同,而且词的构成也要相同。如上例《登高》中的对仗,“无”对“不”,是副词;“边”对“尽”,是形容词;“无边”对“不尽”,又都是偏正式;“落木”对“长江”,都是偏正式名词;“潇潇”对“滚滚”,都是叠词;“下”对“来”,都是动词。句子的构成都是主谓式,“无边”修饰“落木”,是偏正式的名词短语作主语,“潇潇”修饰“下”,是偏正式的动词短语作谓语。另外,还要讲究平仄相对。当然,平仄属于诗词的格律知识,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文章中恰到好处地运用对偶,能给文章的语言增色,不仅看起来整齐美观,而且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奏铿锵,便于吟诵,易于记忆,表意凝炼,抒情酣畅,有节奏美和音乐美。所以,在写作中恰当地运用对偶的修辞,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对比 ,则是另外一种修辞方式,虽然都是两两相对,却有本质的不同。对比的特点是内容上的“对比”,对偶的特点是形式上的“对称”。对偶是从结构形式上说的,对比是从意义上说的,它要求意义相反或相近,而不管结构形式如何。还需要指出,对偶里的“反对”(如“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就意义来说是对比,就形式来说是对偶,这是修辞手法兼类现象。
内容提要:骈文中的对偶,自刘勰之后,并不被特别关注,而骈文研究的整个历史状况所显示的,大多在骈文的范畴、历史渊源、名家别集、典故考证等方面。骈文中的对偶作为其文体特征,其在文章结构意义上的作用和诗歌以及对联都有着显然的差异。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学人对于律诗中的对仗与对联中的对仗所持的基本观点认为:律诗的基本句型由“对联”构成,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因此,对联就相当于将律诗中的这种具有“对仗”特点的句型抽取出来的结果。这种观点屡见于各种学术著作的教科书。本文以为,考察骈文、律诗和对联中的对仗结构,将有利于骈文文本和骈议创作心态与契机的研究,有利于律诗与对联写作与鉴赏的深化。
一、骈文的对仗
骈文是讲究对偶的文体,其以文辞精工,声韵和谐以及造语骈丽为基本特征。自汉魏以降,骈文一直是人们用以抒情、申论和序说的艺术形式。骈文的对偶特点在修辞意义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也非常自然宽松。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及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耳。”刘勰强调对偶的形成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天地万物往往生成在矛盾之中,对立存在,他以“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并非刻意求对为例子来说明对偶在文章写作中的自然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丽辞篇》末尾说道:“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佩”。周振甫先生解释说:“《丽辞》即骈文,讲对偶句,所以承《章句》。”①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是就语言的节奏而言的。周振甫先生强调这是“多用四字六字,所以便于构成对偶。古文顺着语气,语言长短错落,多散行。讲骈文的重对偶,讲古文的重散行。不过齐梁时的骈文,在对偶中也夹杂散句,如《丽辞》中‘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即散句”。周振甫先生的这段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构成对偶的文字根本上不需要特别的理由,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于更多都能构成对偶句,四六和骈文比较,则骈文的节奏音韵更为强烈。
周先生以为“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即是散句,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刘勰这里仍然在讲偶句,并且强调自然而不是刻意经营。这和《丽辞》一开篇强调宇宙间事物“支体必双”、“自然成对”的吻合的。周先生在注释中却又说“营:经营,有意制作。丽辞:对偶文。率然对尔:不经意地成为对偶罢了”。②前后的矛盾说明了理解上的不相一致。我们认为,《丽辞》篇主要阐述的是语言而非文体,其对对偶的分类说明即是“内证”,无需申说。当然,六朝骈文经营丽辞以至于靡艳,确实是《丽辞》中所反对的。
从刘勰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骈文中对偶句的操作运用所持的“自然”审美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造化赋形”的本然和预设,即天地自然万事万物的对立和联系。刘勰追述到《周易》之“文言”“系辞”,论其结偶则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用语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这赶时里强调对偶“妙思”。周振甫先生以为刘勰故意用经典中的对偶和骈文中的对偶比较,是别有用心的,以为这和《宗经》的思想一致。③我们以为,这段文字在刘勰的意思看来,与其说是“宗经”不如说是“神思”。《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始终把对偶作为一种行文的操作手段,而这种手段得依靠“妙思”来进行架构。如果说这是给六朝骈文靡艳之病开了一剂药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处方则是:“积学”、“富才”、“神思”。对空乏而徒有形式的六朝骈体文风的解剖,刘勰是从对偶的分析切入的,但是,刘勰也没有忘记写作主体“驭文谋篇”时“神思”的再次提醒。在《丽辞》中,刘勰接着“妙思”之后说:“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纪晓岚评为“精论不磨”。④刘勰在这里仍然在强调对偶运用的规则和前提在于:“深采”“逸韵”、“合趣”、“契机”。几乎所有精妙的骈文,在使用和操控对偶语言时,都必须自然地为整篇文章的立意服务,因此也就使得对偶句具备了内容的延展性、丰富性、联合与统一性。当出现了上句之后,在写作的心态和需求层面上,下一句除了要适应上句的对偶之外,要充分地实现内容的延展与补充,而不能有语义上的“合掌”。并且,所有的对偶必须顺应全篇的情理、事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否则便会断裂和阻隔。例如:《前赤壁赋》开篇即偶,在“壬戌之秋”后点明“七月既望”。遵循“先总后细”“互为表里”的原则。这样的对偶,便顺畅而自然。可以说,骈文写作是在进行“对偶的组装与剪辑”,而主体意识的流动便成为线索。骈文之难,端在于此。所以,刘勰强调“神思”,强调“驾驶”和“谋篇”。
由此,我们可以把骈文运用对偶的几个关键词归纳为:自然、神思、合趣、契机。这种思想在唐宋时期的骈文大家所发展且成就卓然。如王勃《滕王阁序》、苏轼《前赤壁赋》等竟成巅峰之作,脍炙人口。后之骈文,虽篇章累积,然未能超迈,原因在于难能神思,难能契机,虽对偶而未必“合趣”。至清代,骈文创作相抗于桐城派散文而兴起,研究骈文之著述随之丰富。然能振起一代文风者寥寥,及至民国,虽不乏承继者,却又湮没在白话文运动之大潮中,以至于孙德谦、李祥、钱基博、刘麟生、刘师培等人之研究著述,亦传之未远。
二、律诗的对仗
律诗和骈文中对偶的比较结果,是律诗对偶的严格和规范。律诗因为字数少而不允许浪费“资源”,必须节约语言文字的成本,用最少的词汇融汇最丰富的意思。所以,律诗开始把对偶形式严格定义为“对仗”。它不允许像“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样的对偶出现。因为上下对偶中同样的位置用了同样的字。这在律诗中决不允许。
律诗(五、七律)相比较其他如绝句和古风类体裁的诗歌形式而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用对仗,并且必须如此才可以成为律诗。“律”,指的是某种规定性,自唐代以来,音韵规律被人们广泛运用于诗词创作与鉴赏中,成为普遍遵守的法度和准则。格律由三个要素即音韵、平仄和对仗构成,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取径,在于遵守格律并使得语言具有优美的形象,从而创造诗的审美意境。《诗经》以降,音韵的流美与和谐始终是诗人的追求,由此而进一步实现语言的节奏感和对仗的美,则是在近体诗形式完善之后。
五律、七律的对仗要求是:三四句、五六句必须用对仗(颔联和颈联),这已经是常识。作律诗之难端在于此。按一般诗作起、承、转、合的结构要求,通常情况下,用对仗的颔联和颈联恰好处在承和转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往往有一条难以和谐统一的鸿沟,把诗意分割而出现松散甚至断裂的毛病。对仗句型的最基本要求是出句与对句的“工稳”,习惯上为了达到目的,又常常按同一类事物相对,这亦是常识。问题在于,这些用来对仗的事物并不都可以为整首诗的立意与表达服务。于是,在不同程度上便会使得对仗与表意成为矛盾。照顾了对仗的“工稳”则有碍于表意,照顾了表意则又出现对仗“不工”。所以诗家往往慨叹:“律诗最难工矣!”
律诗中的颔联和颈联除了要自身能够自足和谐之外,还要“弹性”地引发下一个对仗句型,或者回应与照顾上一个句型,使之不出现“断意”。因为断意是导致全首诗在情、象、意、境等等方面出现残缺、抵牾、累赘的根源。在同一对仗句型之中,为了求“工稳”,选择事物往往同类,这就容易陷入“合掌”的禁区,造成语词或者句义的合掌,弄出不少的累赘。既浪费了语言,又损害了诗意。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框架内完成好结构的起、承、转、合与语言的流畅、诗意的完美表达,就成为诗家们关注并努力追求的目标。
王力先生在其专著《汉语诗律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中就“近体诗”的对仗及其种类、讲究和避忌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王力先生着眼于对仗的语言层面的研究,认为律诗中的对仗无非有“工对、邻对、宽对三种”。所谓“工对”即是同类相对,如人伦对人伦,地理对地理,天文对天文。所谓“邻对”即天文可以与时令相对,器物可以与衣服相对。所谓“宽对”则是只要求词性相对而不论门类了。王力先生说:“工对最好的‘妙手偶得之,’……在不妨碍意境的情况下,尽可能求其工。”(《汉语诗律学》173页)
通常情况下,人们论诗之“工”与“不工”,往往考察其对仗中“属对”的语词细节,而很少涉及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诗歌意象的和谐与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最佳表达。创作律诗是不允许浪费词句的,如果对仗“工稳”了而诗意却有“疣赘”之嫌,也不可取。我们来看看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中所选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七律《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诗中的颔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若要论其对仗,李白的“属对”不可说“不工”。但是,就全诗而言,这两句实际上只说了一个意思,在意义上已经“合掌”。金性尧先生注解说:“吴宫,三国时孙吴曾于金陵建都筑宫。晋代,指东晋,南渡后也建都于金陵。衣冠,指当时名门世族。成古丘,意谓这些人物今已剩下一堆古墓了。”(《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241页)用两句诗来表一个“意”,李白也太不“惜墨”了。再看毛泽东的一首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诗中的颈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对仗是何等的“工稳”,但是,毛泽东犯了和李白同样的毛病。将“英雄豪杰”撕开来用,本已经有“生硬”之嫌,复又以虎豹与熊罴相对。两句之意无非是说:英雄豪杰为了革命,为了解放而英雄斗争,对虎豹熊罴之类的恶势力无所畏惧。其实,用其中一句就足以表现了。“见微智著”、“管中窥豹”足可以表达,何必将汉赋的铺排手法于律诗中用之,并不宜于表情达意之洗炼。
在这方面,杜甫的七律“登高”或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老杜的写法是比较注意对仗的“弹性”的,颔联以“落木萧萧下”对“长江滚滚来”,老杜心中的悲凉意绪从语言的张弛之中体现。就对仗的词类而言,并不求狭义的“工”,只为了表达所需而展开。颈联的对仗则出现“万里悲秋”对“百年多病”,把空间与时间都考虑到了,诗意在这一横一纵的审美维度中展开,那无边的苍凉与悲叹令人震撼。
我们发现,老杜在颔联中以“无边”、“不尽”对仗时,非常那地承接了首联的“风急天高”和“渚清沙白”。同时又转入颈联的“万里悲秋”与“百年多病”的主体感受,虚实相生,前后呼应。前面的“无边”以“万里”相应扣,“不尽”以“百年”相回答,“落萧萧下”的空间所见,“长江滚滚来”则又是时间的象征。并且为尾联的“合”构筑了情感抒发宕跌的基础。使得整首诗的审美境界悲壮幽远,沉郁顿错。杜甫运用对仗呈现出的是一种“网状结构”,正好切合了易学原理,阴阳互动,交错互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一联之中的自足与统一之外,又兼顾了另一联的“承传”。这才是创作律诗的关键所在。可惜,长期以来,人们多不见此匠心,更多地陷入了某种“套板反应”而自拔不了。需要注意的是:律诗中的对仗,只是一种修辞技巧。其不仅仅为实现对立统一的诗意服务,更为实现诗意的“承转”服务。律诗中的所谓的某一“联”,只是全诗的一个“意象的子系统”。它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脱禽全诗的语言大环境,如果真要抽出去独立表意,也只是极少的、特殊的情况。
三、对联的对仗
对联作为中华文化中的“轻骑兵”,以其自由、轻便、灵活、典雅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其文化根源的发蒙,可以上溯到先秦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去。拙文《略论对联与桃符的文化内蕴》(《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五期)已对此有过论述。对联艺术中或潜或显的蕴藏着一种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构成了对联的形式框架和审美原则,对联的对仗因此有别于律诗的对仗。
对联的对仗本身是一种思维和创作所依赖的形式,两支联语相骈而出,构成独立完善的艺术形式。如果从文学层面去考察,其审美功能是通过语言的对仗和上下联语意义的和谐统一来实现的,对称的美是对联的形式美学特征。
对联的对仗要求比起骈文和律诗来更为严格,“工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较短的对联中,尤其要求严格。因为要实现独立自足的美,所以要创作既“工”且“美”的短联就绝非易事。某种程度上说,对联的创作比诗歌的创作更难。如果给出十个字,既要对仗又要独立完整地表意,能不困难吗?但如果是骈文或者律诗中的某一对偶句型,则不必要独立也不可能独立,它作为整篇文章或者整首诗歌的就绝非易事。某种程度上说,对联的创作比诗歌的一个局部,将为另外的部分腾出空间,或者等待另外的部分来共同构成和谐的“系统”。显然,对联和律诗中的“对仗”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仅仅在语言层面上去研究和认识。而应当深化到更高的的美学层面。因为,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联,对仗的修辞意义被淡化,结构意义被加强。上下联语中的语言技巧无限丰富,或赋、或兴、或比、或拟人、或夸张、或排比、或抒情、或议论、或描写、或说明,如孙髯的大观楼长联,简直就是一篇对仗框架上的绝妙美文。
长期以来,因为忽略了这么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差异,认为从律诗中抽取出对仗的两句即是对联的说法,实在是误导了不少读书人,最终是写诗的问题出了不少,写对联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鲁迅的老师出一句“独角兽”,鲁迅对之以“比目鱼”的故事早被收入典籍,奉为“绝妙好联”,成了学习的范本。那个用来考学生的“孙行者和胡适之”的个案,也被传为佳话。本人没有要贬低前辈的意思,倒是认为,那些误把“文字游戏”当作经典的鉴赏家们应该休矣!因为这种仅仅只具有“对仗”特点的东西,是登不上审美的艺术高台,给人以享受、美感、娱乐的教化的作用的。
结语
总之,骈文的对偶要求宽,随着文章而铺排,其服务的结构宏大,造语以自然、契机为妙。律诗中的对仗强化了修辞意义,但严格而难工,其对仗形式是相对开放的、局部的不独立的系统。对联中的对仗注重结构意义和文体特征,是相对封闭的、整体的、独立的系统。
今古是时间概念词语,且两个字的字意正好相反。所以一般可使用时间、空间、方位概念词语,并且字义也最好相反的词语,与之对仗。比如:中外、天地、先后、长短、高低、南北、东西等等。当然,也可以灵活掌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其他概念词语,但是两字的字义最好相反。
成今古加了一个动词,要形成对仗的话,也需要使用一个动词。但是具体用什么字,需要根据完整的对联语境来增加。
比如,书房对联佳作集里,有一副用苏轼诗词作品集句的对联:
上联:坐觉俯仰成今古;
下联:更论甘苦争媸妍。 (媸妍:丑陋和美丽)
又比如,岳阳楼对联集锦里,有一副:
上联:吴楚剩山残水,成今古战争场; (备注场古音是平音,这里只能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拼音音韵,发第三声仄音)
下联:湖湘骚人墨客,赋先后忧乐词。
以上仅供参考。
对偶通常是指文句中两两相对、字数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对、意义相关的两个词组或句子构成的修辞法。 对偶从意义上讲前后两部分密切关联,凝练集中,有很强的概括力;从形式上看,前后两部分整齐均匀、音节和谐、具有戒律感。严格的对偶还讲究平仄,充分利用汉语的声调。
特点:(1)上下句字数相等。
(2)上下句意思相近或相反,有时上下句意思上具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
(3)上下句对应位置的字眼词性相对、结构相同、平仄相对、不重复用字。
例如:“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例如:石间溪流脉脉,如线如缕; 水塘碧波闪闪,似锦似缎。
关于唐诗:
所谓的唐诗只是对朝代的限定,但不是对体裁的,诗按照体材的不同,可以分为律诗,绝句,古诗等。而对偶是诗词写作的一种修饰手法,在律师的二,三联中的是对仗,与对偶得意义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偶作为一种修辞,可以用在唐诗中,例子数不胜数,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同样例子也是多如牛毛,因此,看对偶还是要看作者怎么用,不能单纯说唐诗都是对偶
本文2023-08-04 10:27:0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9525.html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