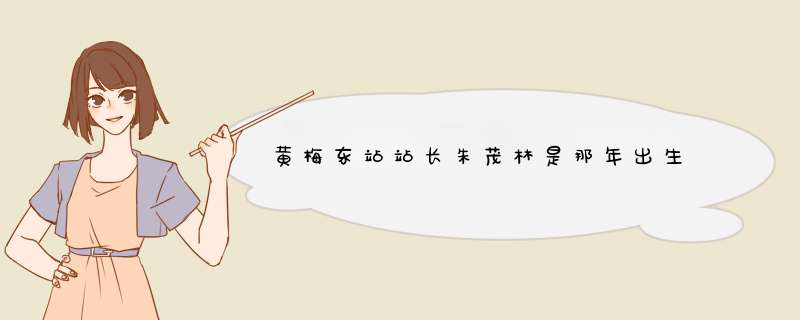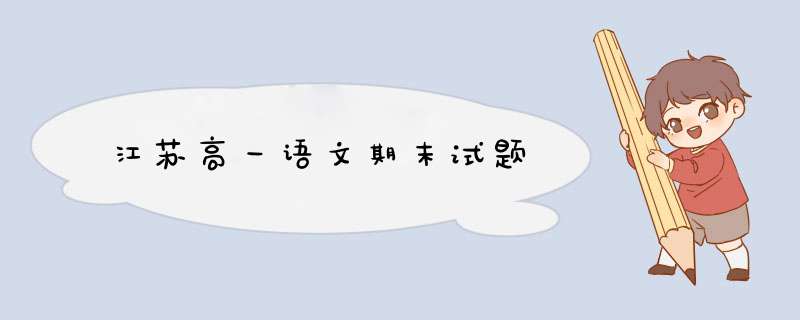讹误的解释讹误的解释是什么

大熊猫被称为国宝的原因:野生数量少、存活历史悠久,是属于孑遗物种。
大熊猫(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属于熊科、大熊猫属的哺乳动物。仅有二个亚种。雄性个体稍大于雌性。体型肥硕似熊、丰腴富态,头圆尾短,头躯长12-18米,尾长10-12厘米。体重80-120千克,最重可达180千克。
体色为黑白两色,脸颊圆,有很大的“黑眼圈”,标志性的内八字的行走方式,也有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大熊猫皮肤厚,最厚处可达10毫米。黑白相间的外表,有利于隐蔽在密林的树上和积雪的地面而不易被天敌发现。
大熊猫的分布地
生活在海拔2600-3500米的茂密竹林里,那里常年空气稀薄,云雾缭绕,气温低于20℃。有充足的竹子,地形和水源的分布利于该物种建巢藏身和哺育幼仔。大熊猫善于爬树,也爱嬉戏。爬树的行为一般是临近求婚期,或逃避危险,或彼此相遇时弱者借以回避强者的一种方式。大熊猫每天除去一半进食的时间,剩下的一半时间多数便是在睡梦中度过。
在野外,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4个小时。大熊猫99%的食物都是竹子,可供大熊猫食用的竹类植物共有12属、60多种。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18-20岁,圈养状态下可以超过30岁。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即国兽,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
大熊猫的命名
大熊猫的近代名称(即中国国内通行的名称),最初定名本叫猫熊或大猫熊,意思是它的脸型似猫那样圆胖,但整个体型又像熊,有的甚至把它隶属于熊科。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前,汉语的书写方式是直书,认读是自右到左,而改为横书后则从左到右,当1939年四川北碚博物馆展出时说明标题用横书,名猫熊,而当时参观者习惯了直书自右到左的认读,误认为熊猫。
自此,首先在主产它的故乡(四川),长此以往向传讹误,久之也就习以为常的把猫熊更名为熊猫了。以后,它通用的中文名叫大熊猫,也就被人们所公认。它的地方名,在它的故乡里多叫白熊、或白老熊,也有叫花熊的。
在岷山藏族地区叫荡或杜洞尕(gǎ),平武白马达布人则叫洞尕;凉山彝族叫峨曲。所有这些地方名,虽称呼不同,而其含义与古籍中叫的貔貅或貘,无非都是说明它的体色白,或黑白,或体型似熊。
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全盛阶段,产生了所谓“汉学”。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乃至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都为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风所笼罩。高踞庙堂的程朱理学败象毕露;由空返实的乾嘉汉学蒸蒸日上。“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拔宋旗,立汉帜,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堪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汉学”是相对于“宋学乙—宋明理学而言,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说。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汉学不同于以往其他思潮和学派,就其学术宗旨而言,称为“汉学”;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言,称为“朴学”或“考据学”;就其时代而言,又称为“乾嘉汉学”。
乾嘉汉学的形成。
乾嘉汉学的勃兴并最终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百年间学术的主流,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汉宋学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更迭,既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内在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
乾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步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亦趋缓和,加之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安抚拉拢与压制扼杀,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气象被顺、康两朝迭兴的文字狱彻底摧毁。在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古籍的政策引导下,士大夫逐渐转向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诠释之上。
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随着理学的衰微及动荡的社会更替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波,学术思想界酝酿着新的思潮。这一思潮以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形成了具有鲜明批判理学色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这一思潮提倡经世济世之学,打破了宋明理学在几个世纪中对思想界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创立出反映新的经济因素的新的理论,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只能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浓厚的法古色彩,导致了清代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
乾嘉汉学的初兴。
继明末清初经世之学大师黄宗羲、顾炎武之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万斯阿、姚际恒、顾祖禹等人,作为清代汉学的先驱,开启了强调通经,重视实证,却拘守烦琐、法古色彩浓厚的乾嘉汉学的先河。
汉学发轫之初,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自励,“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且淹贯群山,博学多能,长于考证。阎若璩、胡渭对《河图洛书》的辨伪,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毛奇龄的《四书改错》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学者,开始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趋势。
乾嘉汉学兴起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胡渭做《易图明辨》,消除了易经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证明了“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皆由此出。《河图洛书》是道士的修炼术,对“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的《河图洛书》给予无情的打击。“宋学已受致命之伤”。阎若璩做《古文尚书疏证》,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中提出详实的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而“祛千古之大疑”,“古今之伪乃大明”。胡、阎二人的著作,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整理古文献方面为以后的汉学家提供了例证,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敢于大胆怀疑权威的精神,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胡、阎二人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开启了一代汉学的风气,他们在治学上侧重于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既未打出“汉学”的旗罐,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之谰言”。
乾嘉汉学的鼎盛。
乾嘉汉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其名,任裁断”。“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的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乾嘉汉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已臻于鼎盛。
吴派代表惠栋(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在家庭浓厚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惠栋的学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治经从研究古文字人手。他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一点成为以后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蒯。惠栋针对魏晋以来对经书牵强附会,随意曲解,甚至篡改经籍,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的浮夸玄虚的学风,强调治经、学经必须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以消除长期以来随意主观附加在古书中的误解和歪曲。在惠栋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下,清代汉学家对古籍进行了广泛、深入地重新注释校订,更正了大量错误,使原来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小学”在清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二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弃了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代经学中去。从反宋走向复汉,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惠栋一生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使绝者“千有五百余年”的汉学“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惠栋在对汉学搜辑钩稽中,不免受汉代糟粕思想的影响,正如《四库提要》中对惠栋的评价,“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在惠栋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学生沈彤、余肖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及大所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恪守其尊汉的学术路径,成为汉学中吴派的中坚力量。
皖派的代表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不仅是清中叶乾嘉学派中最突出的学者,而且多次著文,抨击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戴震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一,重视小学和考据,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上做了突出的研究。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功夫入手,在治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二,戴震作学问,强调“志存闻道”。不只是停留在对古籍字句的校勘证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君子务在闻道”。对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不仅是一部对《孟子》进行考证注疏的著作,更是一部“正人心”的哲学著作。戴震在“志存闻道”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通过理、气这一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理先气后”之说,阐发“理在事中”的唯物观,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
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多治《周易》、《尚书》;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擅长三礼,尤精小学、天算。吴派完全遵循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提倡“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废”,主张复古,“治经求其古”,唯汉是好,唯古是信;皖派吸取了吴派的长处,融惠学为己有,将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与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导义理”,强调求实,“治经求其是”,识断精审。两派以训诂入手治经,在学术渊源上,一脉相承,但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当然,吴、皖两派并不能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同样治经学,顾栋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礼》名家,非惠、戴所能比拟;同样治史学,全祖望、那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皆独辟蹊径,非惠、戴所能拘囿;此外,乾嘉儒臣,朱筠、周永年、纪昀、陆锡熊,阮元等博学多识,其学亦不在惠、戴范围之中。当然,“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这一根本点,是乾嘉汉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的余脉及成就。
乾嘉汉学在戴震时达到顶峰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戴震的后继者分成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继承了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对戴震所注重的“义理”避而不谈;另一派以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兼治音训考据及义理之学,在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中,议论渐渐平和,走上汉宋合流的道路。
乾嘉汉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经学。乾嘉汉学之于经学,潜心整理,尤称专精。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二、文字、音韵学。由于汉学家治经、说经必由文字的音韵训诂入手,奉“读书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字始”为圭臬,音韵文字之学因之而昌盛。三、校勘辑佚。乾嘉学者视校勘辑佚为专门学问,竭毕生心力于其中,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学方面对两汉经师、经说的表彰;史学方面对两晋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辑录;文学方面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苟子》、《墨子》、《管子》三书及有关古籍所取得的成就为历代学者所不及。四、史学。乾嘉学派治史犹如治经,注重总结整理。特别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讹误,或订正其史实,或补辑其遗阙,或整理其故事。在整理古籍中,崇尚求实考核而不主张议论、褒贬。
清代的汉学家们以极深厚的功力和极扎实的态度,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荜路蓝缕的工作,剔除了两千年来对古籍的歪曲和误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复古主义和烦琐主义,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历史转折再次到来之际,乾嘉汉学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现实、提倡经世的今文经学的兴起。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只有少数学者,如俞樾、孙诏让继承了乾嘉大师的遗续,保持朴实的学风,在专业领域中作出了贡献。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今疑义举例》;孙诏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等,作为乾嘉汉学的余脉,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终究无法与已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今文学派相抗衡,汉学已走完了全部的历史路程,走向了终点。
本文2023-08-04 10:29:1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9542.html
- 108484-新刻劍嘯閣批評東西漢演義5_劍嘯閣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85-新刻劍嘯閣批評東西漢演義6_劍嘯閣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86-新刻劍嘯閣批評東西漢演義7_劍嘯閣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87-新刻劍嘯閣批評東西漢演義8_劍嘯閣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88-隨煬帝艷史1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89-隨煬帝艷史2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90-隨煬帝艷史3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91-隨煬帝艷史4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92-隨煬帝艷史5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
- 108493-隨煬帝艷史6_齊東野人騙演天一出版社 .pdf